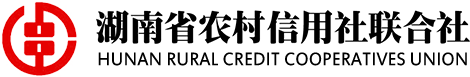夜 雨
入秋了,我却还没有什么季节变换的实感,不知道是不是天气持续高温的缘故,感觉盛夏还是昨天的事。窗外的秋雨混合着蝉鸣,深夜我打开房门去洗漱,外面竟也如同房内一样凉爽,不过之前落了几场雨了也在情理之中。我像平常一样拿着牙刷左右走动,腿时不时抖一下,厕所里很多蚊子,即使这样做也不一定能躲过叮咬。刷着刷着,我发现不用抖腿了,耳边并没有蚊子嗡嗡作响,只有牙刷清洗的震动,像是被突然翻了一页的书,蚊子也仿佛一下子消失了,我站在房门口,对于换季才有了实感。原来,已经入秋了。
前些日子回家时,偶然看见路边的石榴花,开的火红,十分抢眼,正如杜甫所写“江碧鸟逾白,山青花欲燃。”我想起了外婆家的那两颗石榴树,一到盛夏绿叶中就探出那火红的颜色,石榴花瓣柔软轻薄,风一吹就如火焰跳动,它的花萼却厚实坚硬,紧紧包裹着花瓣的根部,待到结果又像一顶小皇冠似的顶在果子的头上。我儿时嘴馋得很,很喜欢吃石榴,每次同母亲回外婆家,一看到石榴花开放,即使顶着滚烫的太阳,我都忍不住过去数花朵的数量,脸上的肉把原本不大的眼睛挤成一条可怜的小缝。这时我外公就会不住的叫我回屋歇凉,嘴里念骂着“魔王”“报应”之类的,等到我数完,脸就晒得跟花似的通红。我外公是个怪脾气的人,他对家中子女很好,在那个重男轻女严重的时代,他愿意卖掉沿街的店铺也要供三女一子读书。不过他同谁都不太处得来,小时候也不见他带着我去找过什么朋友拜访。寒暑假天气不好时,同他争看电视节目,天气好时带上我去田野里放鸡,外公拿上长长的竹棍,搬上一把椅子坐在中间,时不时敲敲打打,防止鸡跑出太远,而我就在田地里追逐着鸡群,这样一下午也不觉得无聊,只觉得天地辽阔。待到金九银十石榴就成熟了,我外公总是摘下后藏在他的宝座下面,等到我来就拿出来给我吃。他宝座下面也藏着不少其他好吃的中式糕点等我“探险”。拨开石榴坚韧的外皮,里面如宝石般的石榴籽便显现了出来,在阳光下通透莹润。我吃石榴不太讲究不吐籽,一把塞进嘴里嚼出汁水就囫囵吞下了,外公看到又开始念骂不像女孩,邋遢大王什么的,我也不介意,看着电视手上拿着吃到一半的石榴,身边堆着好些个还没动。晚上我自觉让出电视节目换台权,同他一起看抗日电视剧。等到节目结束,人也倦了,熄灯后我有些睡不着,吃太多积食了,我偷偷睁眼看向窗外,屋外明月高悬,屋内月光穿过叶片的间隙落在桌上,地板上,树影斑驳,风移影动,珊珊可爱。夜深了熬不住意识就开始迷糊,火车哐哧哐哧的声音忽远忽近,不知何时便沉沉睡去。
余华曾在《第七天》中写道: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,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。外公走时我还在大学的课堂,母亲打电话告诉我时失声痛哭:“我没有爸爸了”,是啊,她不仅是我的母亲也是外公的女儿。正如《百年孤独》所写,“父母是隔在我们和死神之间的帘子,你和死亡好像隔着什么在看,没有什么感受,父母挡在我们中间,等到父母过世,你才会直面这些”。在那天,母亲失去了爱她的爸爸,我失去了爱我的外公。等我匆匆赶回家,外公安息在堂屋的地上,我走过去握住他苍白的手,看着不再起伏的白布却没有他已经逝去的实感,我难过但没有心碎,因为我总觉得他并没有离开。令人窒息的梅雨季过去,我的肺部还隐隐残留着潮湿霉烂的水汽,直到看到路边的石榴花,又是一年,今年也没有人摘了家里的石榴等我回去了。
天井旁没有蝉鸣,仿佛只那扇门就跨过了夏季,我缓慢擦拭着我的牙齿,听着没有蝉鸣的雨声,夜色和寂静的秋雨笼罩着我,我沉默地听着,我想可能以后再也没有这样寂寥的夜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