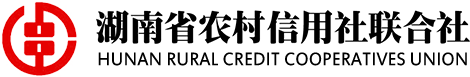摆渡人 ——基层柜员普通的一天
“船来了,快点快点”“老陈,慢点,等我一下”……一看手机,还不到五点。这一声声的吆喝就像一枚石子,猝不及防地投进了尚未完全苏醒的寂静里,漾开了一圈圈愈来愈嘈杂的涟漪。我在这农商银行小网点的二楼宿舍里,被这潮水般漫上来的声浪推醒。不用看日历也知道,今天是赶集的日子。这声音于我,比任何钟表都准。
说是“乡”,其实早些年撤乡并镇后,这片地界上,就只剩我们这栋两层小楼,还被村民念叨着“公家单位”的名字,像河滩上一块倔强的石头,守着日渐荒疏的旧河道。
隔着窗户玻璃,天色是鸭蛋壳般的青灰。声音却是活色生香的:摩托车“突突”的排气声,扁担摩擦的吱呀声,女人高声唤着落在后头孩子的名字,男人粗着嗓子谈论昨夜打牌的输赢……这些声音交织着,由远及近,又由近及远,朝着同一个方向流去——河边的渡船。这里没有桥。附近五个村子的人,都要靠两条渡船把自家田里摘下的青椒、茄子,院里啄食的鸡鸭,以及一个清晨积攒起来的、热气腾腾的盼头,一担一担地,“摆渡”到河对岸那个更热闹的市集上去。
虽然醒得早,但还是得到八点开门营业。我下楼,拉开厚重的卷帘门。第一个身影就挤了进来。是东村的张爷爷,他裤脚还沾着泥点,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个裹了好几层的塑料袋子,取出皱巴巴的存折和户口本,隔着柜台玻璃递给我,声音有些发怯:“帮忙取粮补……”
接下来的几个小时,便在这方三尺柜台后,陷入一种专注而重复的“摆渡”。取粮补的,取老人社保的,存卖粮款的……几乎都是老人。他们大多不记得密码,或者指头粗裂,按不准那小小的键盘。我便一次次探出身去,隔着玻璃指点:“按‘确认’,对,绿色的那个。”“再输一次,不急。”他们的脸,紧贴在玻璃上,像看什么精密仪器般,紧张地盯着我每一个细微的动作,直到钞票从出口“沙沙”地吐出,那紧蹙的眉头才豁然舒展,那笑容里有放下心来的轻松。
存折上的数字,大多很小。但那一笔一划的确认,一次一次的指纹按压,对于他们,却郑重得像一种仪式。我不是在发放钞票,我是在帮他们,把国家一个宏大的、温暖的政策诺言,从纸上“摆渡”到他们粗糙的、布满沟壑的手心里。玻璃内外,是两个流速不同的世界。外面是滚烫而喧腾的生活之河,里面是冷静而规则的数字之河。而我,是这渡口上的摆渡人。
晌午过后,河对岸的喧嚣渐渐沉淀下来。赶集的人回来了。他们不再急着挤到窗口,而是三三两两,聚在银行门口那棵老槐树的荫凉下,我的业务也稀疏下来,能够有空闲和李大娘王大叔扯着各村的家长里短。日头偏西,金光斜斜地切过柜台,把屋檐的黑影拉得老长,印在柜台上像一道栅栏,也像一道坚固的堤坝。送走最后一位客户,锁好钱箱,拉下卷帘门。世界“哗啦”一声,仿佛被关在了外面,又瞬间静了下来。
我走上二楼的阳台。大河在暮色里变成一道暗沉沉的银练,对岸集市早已散尽,只剩空荡荡的码头。而这边,村落里升起了几缕淡蓝的炊烟,温暖而踏实。渡船正突突地,从对岸载回最后一批归人。我忽然觉得,自己这方小小的柜台,何尝不也是一条渡船?清晨,我将他们渡向对岸充满希望的集市;整个白日,我将远方的政策、国家的信用,一笔一笔,渡进他们当下的生活里;而在这傍晚的闲谈与未来的期许里,我或许,也在参与将他们今日的劳碌,悄悄摆渡向一个更有奔头的明天。
风起了,带着河水与泥土的凉意,我转身回屋。屋里的灯光将这小小的网点,映成一枚在渐浓的夜色里,安静而笃定的印章。明天,最早的一班渡轮,又会载着那些沾露水的蔬菜和热切的脚步,从对岸驶来。而我的摆渡,也将再次开始。在这片被大河隔开的土地上,我们各自摆渡,又互为彼岸。
- 上一条:张家界农商银行:以青春践初心,以成长赴使命 2025-12-15
- 下一条:温暖乡邻,情系柜台 2025-12-1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