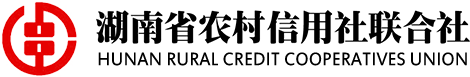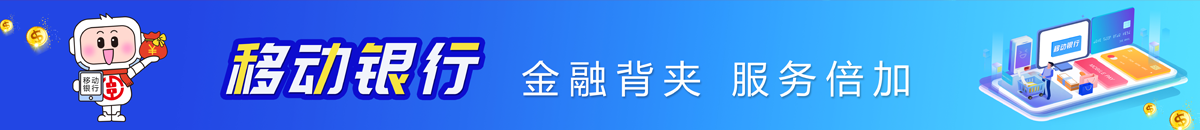执笔为桥—一位青年写作者的乡土情结
我是谢子尧,一名扎根在安化山水间的普通青年。2022年,我从湘潭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毕业后,带着“服务家乡”的初心加入安化农商银行。三年时光里,我既是金融柜台后的服务者,也是应急救援一线的记录者,更是文字江湖里的追梦人。扎根农村,服务基层让我对“青年担当”有了更深的体悟——青春的价值,在于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需求,用不同的方式为这片土地注入温度。
为何执笔写作?
我的答案总与一片茶叶有关。
在安化的深山里,茶农们常说:“一片叶子落入杯中成了茶,落入土里就成了根。”而我的文字,恰似那片既想沉入泥土、又想浮向远方的叶子——扎根于农商行的服务日常,飘向更广阔的乡土人间。
写作是“看见”的修行
写作,需要在生活与工作中多一双“眼”。泛黄的存单、新签订的贷款合同,每月一汇的养老金,每天经手的这些票据与数字背后,藏着太多未言说的故事。这些碎片,在业务系统中或许只是几行代码,但我的眼中,却是时代浪潮下的个体史诗。一张存单,是在外务工日日夜夜的艰辛,一笔贷款,是创业之路的信心与坚决,一张社保卡是国家落地的惠民举措。
我开始带着“人类学田野调查”般的自觉去工作:记录方言中鲜活的金融隐喻,收集乡亲们对“普惠金融”最朴素的解读,甚至从老人皱纹的舒展来判断服务满意度。有人调侃我“不像柜员,倒像记者”,但我知道,唯有先俯身“看见”尘埃里的光,文字才能拥有穿透人心的力量。
写作是“缝合”的使命
在安化我常常目睹这些割裂,通过手机银行足不出户办理金融业务的年轻人,与攥着银行卡不敢用ATM机的老人共存。
这些割裂让我意识到:飞速发展的时代,需要有人为断层中的群体架设理解的桥梁。
于是我的笔成了“针线”。
我将晦涩难懂的金融政策文件转化成耳熟的乡音,将金融知识编进一个个乡土小故事当中。有读者留言,普惠金融原来不是文件中的术语,在我笔中成了一幕幕鲜活的金融场景。这让我更坚信:作家的责任不是制造晦涩的鸿沟,而是用乡土熟悉的语言,缝合传统与现代的裂缝。
写作是“种籽”的远征
成为县作协会员时,前辈赠言:“莫做花瓶里的观赏竹,要当岩缝里的野山松。”这句话成了我的创作信条。
我不再堆砌辞藻,无病呻吟,我倾心去记录那些正在改变土地的种籽。去记录自掏腰包为村民修路的养殖大户,去记录将产品销往国外解决村里百余人就业问题的创业模范,去记录返乡创业种黄精的“00后”新农人。这些真实的故事发表后,更多年轻人开始重新打量脚下的土地。最让我触动的是,我将孤寡老人“秀阿婆”的故事发表后,引起许多人对孤寡老人生存困境的关注,更有人通过互联网找到我,要对老人进行资助。这让我想起泰戈尔的诗:“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你,而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。”或许,这便是文学最美好的抵达——不是施舍感动,而是唤醒更多人成为光的本身。
有人质疑:“银行人的写作是否不务正业?”我的回答藏在三个比喻里:笔是显微镜,在重复的日常中洞见人性的幽微,让冷硬的金融数据有了体温;墨是粘合剂,将政策文件翻译成田埂语言,让国家战略与个体命运血脉相连;纸是播种机——把安化的故事装订成册,让散落山野的微光汇聚成星河。
4月16日。我参与《湖南文学》主办的基层改稿会,使我对文化引领乡村振兴的理解更为深刻。我愈发清晰:青年作家的笔,从来不应是孤芳自赏的装饰品,而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,或许撬动的幅度很小,但至少能让某个角落发生向好的位移。
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坚守,做时代的记录者。去写智能柜台前颤抖着按指纹的老人,去写无人机喷洒农药时田垄间惊飞的麻雀,去写每一个在乡村振兴路途中披荆斩棘的奋勇者。
要记得: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字,终将成为后人解读乡村振兴的底本。每一笔落下时,都该带着对土地的敬畏,以及对未来的温柔预言。
做一只夜莺,不停歌唱的夜莺,歌唱这自然、灵魂与宇宙。
- 上一条:在农商银行,我学会了耐心 2025-09-22
- 下一条:尽我所能,敬我不足 2025-09-2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