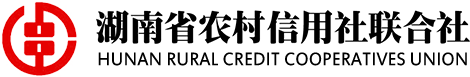岁稔与决算
点击数: 时间:2025-12-30 作者:杨娟
来源:衡山农商银行
当春风还在翻阅土壤的欠条,
他们的算盘已拨响第一颗露珠。
稻种与合同在晨雾中同时抽芽,
指节把利率抚平成沟渠的弧度。
夏日将传票摞成待授粉的禾穗,
汗碱在账页边析出霜花的形状。
催收路漫过三轮车辐条的断点,
总有一枚印章替荒坡按住返青的月亮。
现在秋阳在贷偿表右侧凝固,
他们用冻疮的笔迹搬运年轮——
那些被暴雨冲垮的抵押红砖,
在报表间隙里重新站立成粮囤。
而决算的夜晚,灯箱含满金黄的麦仁,
打印机开始吟唱连绵的穗浪。
当最后一枚指纹在凭证上熟稔绽放,
秒针突然变得比春播时更为悠长。
现在他们终于能望见钟摆那端的薄雾,
未启封的墨水瓶映出初雪与道途。
这些被数字浇灌的、温热的根系,
将在黎明前长出通往春天的复写纸。
而崭新的月份正在装订机里舒展,
像田埂等待未签署的绿意。
他们整理衣领如同校对抽穗的节气,
让所有的辛劳在霞光中,归仓成一声
比桂花更细密的、关于丰盈的颤音。
- 上一条:樟树的落叶 2025-12-29
- 下一条:一年光景,收于账页之间 2025-12-3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