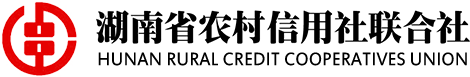追光
早晨六点零三分,第一缕阳光穿透百叶窗的缝隙,落在我的眼皮上。
我眨眨眼,没有立即起身,而是任由那缕暖意在脸上游走。这个冬天的早晨不太一样——空气里没有往常刺骨的寒意,反而荡漾着某种柔软的暖意。窗外的天空是淡淡的粉橙色,像刚切开的水蜜桃。我知道,这是一个珍贵的暖冬日。
我掀开被子,让阳光完整地洒满全身。那一刻,我突然理解了植物对光的渴望——那种从细胞深处迸发的、朝向光源的本能。也许人骨子里也藏着这样的种子,只是在钢筋水泥里埋得太久,忘了发芽的方式。
十点钟,我做了个冲动的决定:今天要做一个追日的人。
来到公园,公园里已有不少像我一样来“采集阳光”的人。老人们坐在长椅上闭目养神,孩子们在草地上追逐自己的影子,一对情侣共披一条毛毯,头靠着头读同一本书。我找到一处略微倾斜的草坪躺下,草尖已经枯黄,但在阳光下散发着干草特有的香气。
正午时分,太阳爬到了天空正中央。我脱下外套,将其铺在地上,顺势而躺,头顶上的鸭舌帽取来遮阳,肆意享受着太阳带来的能量。那一刻,时间似乎放慢了脚步——我能感觉到阳光如何一寸寸移动,如何温暖我的额头、鼻尖、下巴,如何透过衣物渗透到皮肤深处。
突然想起小时候,母亲总在冬日晴天晾晒被子。晚上钻进被窝时,那股太阳的味道总能让我很快入睡。她说那是“阳光被锁在了棉花里”。现在想来,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定期将自己“晾晒”,让光透进那些潮湿的角落。
午后,云层渐渐增厚,太阳开始西斜。我看着天际线处渐渐暗淡的光,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舍。于是我做了第二个冲动的决定:我要追着太阳走,看它能带我去哪里。
于是逃离城市计划启动,我们沿着公路向西行驶,太阳在右前方的天空缓缓移动。这不是一场竞赛,而是一场温柔的告别仪式——我想尽可能延长与光共处的时光。
车过跨江大桥时,太阳正悬在江面之上,将整条河流镀成流动的金色。突然一辆大货车鸣笛,打破这份宁静,从而惊起一群水鸟,它们飞向光的方向,翅膀边缘闪着金光。我停下车,靠在栏杆上看了许久。那一刻突然明白:追光不是要抓住它,而是要让自己沉浸在它存在的每一刻。
终于,在城西的山丘上,我找到了今日最后的观日点。太阳已经触到远山的轮廓,像一颗慢慢沉入深海的橙色宝石。寻一处视野开阔处坐下,如痴如醉欣赏这副景色,看着它一点一点下沉。
最后一缕光消失的瞬间,天空并未立即暗去,而是铺展开一片壮丽的晚霞——粉紫、橙红、金黄交织,仿佛太阳离去前将所有的颜料都泼洒在了天空这块画布上。我忽然理解了:日落不是结束,而是光变换了存在的方式。
夜幕完全降临时,打开车灯返程。前方的路被照亮,而我也成为别人眼中的一点光。那一刻,白天所有的感受汇聚成清晰的领悟:我们追光,不是因为恐惧黑暗,而是因为向往成为光本身。
临睡前,我写下这样一段话:“今日做了一朵向阳花,从黎明追到黄昏。最后发现,光不必始终在外追寻——当我们循爱而行,为所爱之人事物燃烧自己时,我们便已成为那束光。”
关灯后,房间并未完全黑暗。窗外远处的灯光、月光、星光交织成一片温柔的微明。我闭上眼睛,感觉白天的阳光仍在眼皮下隐隐发亮。
太阳明天依旧会升起,而我们都在这样的循环中——追寻光,成为光,传递光——直到整个世界,都变成一个暖冬。
- 上一条:在规矩的代码里,跳一场曳步舞 2025-12-16
- 下一条:张家界农商银行:以奋斗之名,行使命初心 2025-12-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