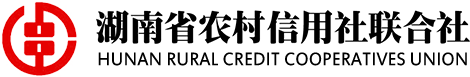雪夜碎语
窗外,下着一场雪。一场反复预告了很多次才上演的、浩浩荡荡的雪。
推窗,暗夜睁开了眼睛,目光尽头,北风和雪花交织,雪光和星光往复,淅淅沥沥,呼呼啦啦,松针,鹅毛,在万奈俱静的寒夜簌簌落下,仿佛一场情绪的双相奔赴,反复否定又确认,走远又靠近,离别又重逢。山巅,树梢,屋顶,草坡,车身,大地……一层白覆盖另一层白,已经蜷缩打烊的某种情感在一阵高过一阵的惊喜中缓缓舒展、打开,像时光隐秘的花朵,只那么一瞬,就轻盈落在了心上,眷刻成无法忘却的记忆。
指尖也温柔下来。炉子正旺。茶壶嘀嘀咕咕,说一些私密的话。烤红薯香了,花生也香了,两盏茶吞云吐雾,纠缠不清,暖,在窗前环绕,冬夜露出它原本的样子。
记忆里的雪夜,是父亲骑着凤凰牌自行车晚归的旧时光,那个印着信用社字样的工作袋端端正正地搁置在车龙头前的篮子里,由一层白雪稀薄覆盖着。听到自行车铃声响起,我们姐妹仨像一片片飞舞的雪花,呼呼啦啦地奔向父亲,隐隐约约的雪光里,父亲一边拿工作袋,一边递给我们一把花生,或者几片麦芽糖,让我们赶紧回屋。
没有花生和麦芽糖时,父亲会在路上摘几枝野菊花给我们当下乡礼物。毕竟是三个女儿的父亲,他比我们更懂我们。
时常,野菊花比花生和麦芽糖更让我们欢喜和激动。
这样的雪夜,一晃就是三十年,直到父亲从信用社退休。
但野菊花点缀生活,表达爱意的姿态却像一粒火种,早早根植入了我的骨血,让我懂得美好,珍爱生活。每年秋冬,野菊花盛开时,我都会采摘一把,放在家里,激活那些压抑的日子。
雪纷纷扬扬,越下越大。
我们围坐在炉前,煮茶,烤肉,闻香,也说春天和人间。
桌上放着一本《意象的帝国》,一本《世间所有的秘密》和一本《民法典》,这是我和正儿准备阅读的书籍。《意象的帝国》已经读了两遍,感觉还不够,还想再读一读。对于这个年岁的我来说,其实早已不在意学会什么了,但读书是必须坚持的。在喜欢的文字里,把自己重养一遍,是一件多么欢喜的事情呵。《民法典》则是正儿的。是他喜欢的漫画版,因为喜欢,所以专注,他风风火火,一口气读到了第八十五页,没抬头。
小花瓶插着几枝野菊花。香气,清清幽幽,淡淡雅雅地飘着,枯燥乏味的生活便一路生花了。
花瓶是正儿从兰州带回来的礼物。去年,十五岁的他一个人去了峨眉山,北京,九寨沟,成都,重庆,兰州,中卫,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他与世界的距离。而我,除了支持还是支持。这是母亲的力量,也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情。
野菊花摘回来有些日子了,它早已不似开始那般鲜活。大部分花朵已经枯萎,凋谢,只有几朵还在枝头激情澎湃,抬头挺胸,憨态可掬。金黄的花瓣,深黄的花蕊,层层叠叠又依次铺开,与它们对视,仿佛看见了另一个自己。
这是今年第二批来我家的野菊花。记得刚拿到正儿带回的小花瓶时,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养野菊花。那个阳光正浓的午后,开车,带着正儿去沙堤大道散步,返程时在路边摘了一把野菊花,像父亲给我们带野菊花那般。
正儿开始是抵触的,他反复强调,野菊花要在它适应的环境里生长,采摘回来就破坏了它们的生长规律,养不活的。
可我还是想要独占它的美。想像小时候那般把野菊花养在家里。
我安安静静又可怜巴巴地看着正儿,他只好让步,让我摘。摘一枝。
可既然下了手,岂能是一枝了结的?所以,一股脑儿的两枝三枝四枝……直到满满一大把才收手。
带回家,我小心翼翼地伺候着,剪枝,整理,换水,加营养液,像伺候祖宗一般。
它们也很懂我,在小小的花瓶里,铆足干劲,精神抖擞地伸开手臂,露出笑脸,挨挨挤挤又华华丽丽地绽放着,盛开着,它们比小时候的那丛野菊花更浓烈,似乎要给我一个完整的秋天,直到半个月后才开始有一朵没一朵的凋零。分着批次,不容察觉。等我发现时,它们已经单方面结束了这美好的约定。
我不甘心它们的离去,又从后坪摘回了几枝。我要延续这份秋天的美好,像延续父亲的爱。
这一次,我伺候得更细了,也关注得更多更久了。
我时常长时间看着它们,毫不吝啬地对它们说:爱你。
它们一改往昔,它们不负重托,它们长长久久地开着,开着,一直开到了大寒这一日,开到了这
幽静的雪夜,和父亲带给我们的那把野菊花重合。
窗外,雪依然在下。熙熙攘攘,悉悉索索。
推窗,那片白色世界就进了我的世界,激情满满,满心欢喜。
炉子正咕咕冒着热气,像温暖人间的絮语。
我边听着簌簌落下的雪声,边闻着野菊花的幽香,回忆着,碎碎念着。它们不像诗,也不像散文。它们只是一些闲散的文字。而这些闲散的文字,是自然流淌的、最真实的自己,是爱与暖的传承,不卑不亢,清澈善良,一如独一无二的我们。
- 上一条:指纹的温度 2025-12-31
- 下一条:没有了